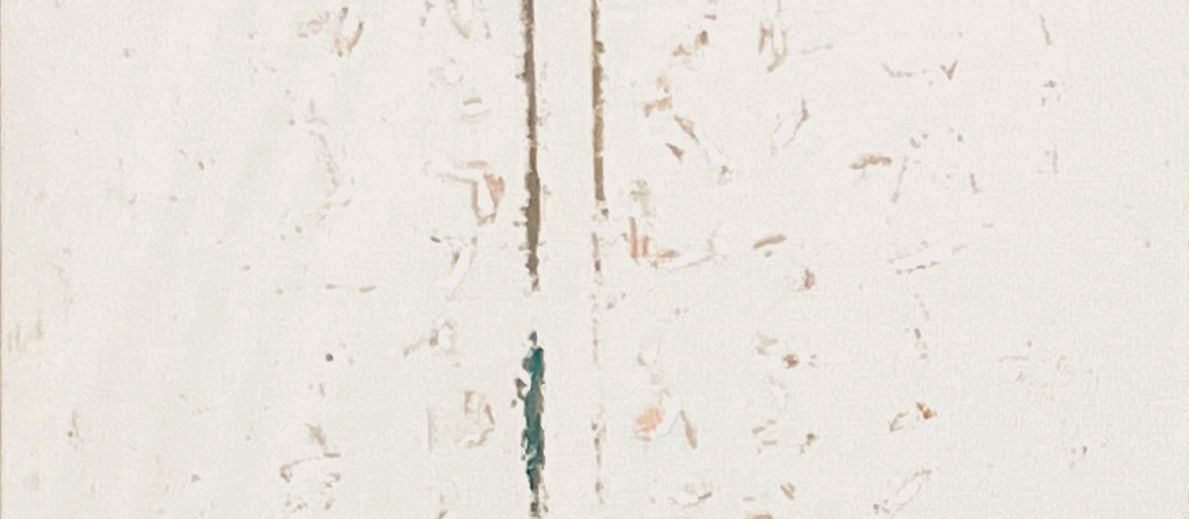
文字之前与之后
2025
创作脉络
谈到文字,东亚艺术家们很难不联想到书法,一个传承了几千年的象形文字的“妆造”热情,像基因一样早就编码在东亚艺术家的血脉里,即便是在当代艺术背景下的今天。我也不例外。
我一生都和文字痴缠,文史哲诗意义层面的先不说,和视觉和体验相关的如下:一个很棒的民间书法家的父亲,他的字曾在周边很多家庭和工厂的门楣上悬挂,这足以支撑起我自视颇高的童年;家族厄运令我的青少年时代忧思重重,抄写艰涩文本一度成为我压制浮躁进入深度学习状态的秘密武器;二十余年职业艺术生涯,传统笔墨誊写佛经让我在难以抵御的寒冬盛夏依然得以安神入定;疫情期间被困于异国斗室,思乡无助时书法再成一剂宽慰良药……
不过,书法不等同文字,书法除了文字的关联,身体践习的关联,还有门第等级制的托底,民族文化的惯性等。而文字,因其与意义的直接关系使得它仅仅在场便是能量!
在现当代视觉艺术领域,文字早就不再单纯以书法的面目介入其中。我在几年前的《窗系列》和《复写本系列》的创作中已经发现,文字不仅可读而且可观,不仅可观而且可感。可观不只因其装饰性(如书法),而是即便意义被暂时遮蔽——例如读者读不懂异国文字或文字被涂抹覆盖扭曲,文字却依然能传递其内涵的能量,文字的在场总是带来神秘的精神张力。即文字与意义之间不仅存在物理连接,也存在那种类似“波”的不易被完全切断的连接。

字痕-3
布面油画,30*30cm
2025
收藏
如果说我最初创作(包括雕塑)是在文化惯性的驱使下不由自主地受到书法(文字的视觉和书写体验层面)的影响;而在《窗系列》之后,我则转向对文字本身的表达(文字的意义层面);而在《复写本系列》中,我又附带探讨了文字互为异质文本和文本重叠带来的可能。
几千年来,文字可以说就是文明的底层代码。虽然印刷术让书法势微、计算机又釜底抽薪了文字的纸张依附,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显化了文字本身在文明中的权重。
如今人工智能正逐步改变知识、技能、逻辑推理对人脑的依存关系,人类借由文字铸基起的意义文明正加速改变。人脑、眼、手协作书写的文字,正日渐失去其原有的光环与敬畏。当文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人脑中“外溢”而出,并在诸多方面在机器中形成了远胜于人脑的表达效率——这种俨然“人造上帝”般的出现,究竟将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爱的惊喜,还是未来未知的不知所措?
以上思考,正是《文字之前》和《文字之后》两个系列作品的潜在背景。作品仍在持续创作中。

红山系列
文字之前
一个沉浸于创作状态的艺术家,和一个独自悄悄走进洞穴涂画的原始人,有什么不同?他们都在尝试用某种尚未成形的东西,去表达内心尚不清晰的感受;他们都在以手的动作,本能地进入一种形而上的思维——这种思维看似无用,却关乎存在:关于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模糊体察,即便他们所做的东西也许具有其他实用功能。
“文字之前”是一个富有意义的命题。它不仅指语言诞生前的远古状态,也象征着艺术创作之初精神火花点燃的刹那。它孕育着哲学与艺术的发生可能,类似现象学的还原。此处的“文字”既代表人类文明的书写语言,也隐喻艺术家独立表达的艺术语言,尤其关联东亚传统中书写即体验的个人实践。在这里,文字的书写行为不仅成为人类文化觉醒的驱动力量,也可能是对未来标准化机器语言的一种强有力的抵抗象征。
文字之前
文字之后
文字是文明的显现。而当文明衰退,文字或许也是最先隐退的存在。人们谈及文明的消失,往往指的是一个族群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与文字。那么,当人类的语言系统最终被机器语言或非人类代码取代后,我们还将剩下什么?
我相信,“后文明”世界依旧会留下文字的痕迹。但这些痕迹不同于自然界的遗迹,它们是曾经随人的手迹舞动的线条,是脱离了意义的形状碎片,破碎却依然显露出对旧有文明秩序的不舍。这些碎片,或许会成为“文字时代”的考古残存。
“文字之前”与“文字之后”在视觉上有许多相似之处,这种相似是合乎逻辑的——一个文明系统的兴起与退场,常常构成一个合龙的圆。但这两个系列真正共同指向的问题是:当熟悉的意义系统不再在场,人类是否还能构想出另一种存在?是否还存在着别样的存在诠释?某种文明样式的退场,并不等于人类的终结。或许真正令我们不安的,不是失去,而是人类正在变异——通往一个也许更高级的自身形态。

线舞系列
线域系列

墨余系列

字痕系列
评析
关于《文字之前》与《文字之后》
罗一的“文字”系列并非关于书法的形式实验,而是一场深刻的哲学探索:文字如何在意义生成与消亡之间,持续成为一种精神性载体。两个系列——《文字之前》与《文字之后》——构成了一个时间上的观念闭环,既指向语言未被制度化的原初冲动,也预设了后文明语境中文字作为文明遗迹的余响。
在《文字之前》中,艺术家回溯语言尚未成形的神秘时刻。图像、手势与精神感知尚未分化,创作是与存在的直接搏斗。那些带有模糊笔触与覆盖痕迹的画面,仿佛在模拟某种原初的、尚未被编码的语言发生现场。
而《文字之后》系列,则面对当下技术文明对语言系统的替代与瓦解。画面中的字符、笔迹与残损痕迹如同文明遗址的碎片,诉说着一个关于遗忘、抵抗与记忆的未来寓言。即便意义本身不再明确,文字的“在场”依然唤起观者的视觉共鸣与精神感应。
两个系列形成一种张力:一端是语言的发生学,另一端是意义的后遗症。罗一将自身书写经验、文化背景与哲学思辨融合为视觉语言,使“文字”成为超越工具性的存在。它既是沟通的起点,也是沉默的见证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